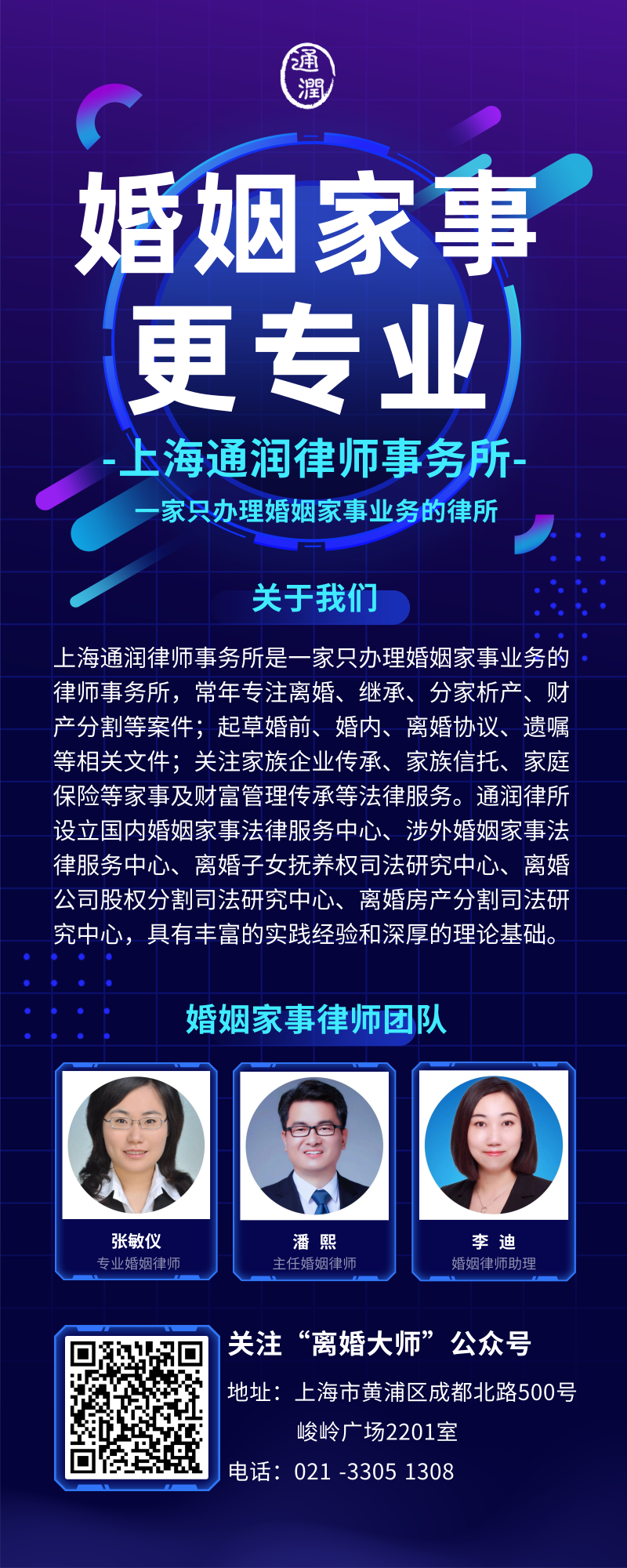分居的法律适用争议及其解析
转载自:人民法院报 家事法苑
周丽华:分居的法律适用争议及其解析
原文标题:分居的法律适用争议及其解析
作者:周丽华,国家法官学院
来源:人民法院报官网,2025年6月19日
原始链接(点击本文左下角“阅读原文”可进入原文界面):
https://rmfyb.chinacourt.org/content/202506/19/article_980064_1391171891_6103415.html
□ 周丽华

在秉持破裂主义原则的离婚立法例下,配偶双方分居满足法定时长,一般可被推定为婚姻关系破裂而被准予离婚。我国即采此种立法例。民法典第一千零七十九条有两款规定与分居感情破裂推定有关:一是该条第三款第四项规定的,当离婚案件调解无效时,若出现“因感情不和分居满二年”的情形,应当准予离婚;二是该条第五款规定的,经人民法院判决不准离婚后,双方又分居满一年,一方再次提起离婚诉讼的,应当准予离婚。相较于民法典第一千零七十九条所明确规定的其他夫妻感情破裂的推定情形,诸如重婚或者与他人同居,实施家庭暴力或者虐待、遗弃家庭成员,有赌博、吸毒等恶习屡教不改等,分居推定更加贯彻无责主义,从理论上来说适用范围最广。然而在实施层面,我国对于分居的细节规定甚少,实践对于分居的认定、分居的时间规定以及分居期间配偶双方的权利义务关系等均存在争议,以下将结合法答网中关于分居的相关提问,对分居的法律适用争议进行梳理解析。
一、分居的认定
“分居制度”亦称“别居制度”,在各国婚姻法上普遍存在。对于多数西方国家而言,夫妻进入分居状态需要法院进行裁判,即使在同时施行合意分居制度的意大利,分居协议也需要法官批准才可生效。在上述制度下,由于分居需要官方法定程序才得以开启,所以分居的时间起点以及状态认定均较为明确。与此相对,我国立法上的分居属于一种事实行为,只能依靠法官在离婚诉讼中进行事后确认,所以分居的认定一方面受限于当事人的举证,另一方面也很大程度受法官对于分居含义理解的影响。在既往的司法实践中,普遍认为法律上的分居需要同时满足客观及主观两个方面的要件:在客观上,夫妻双方需要在物理上分开居住;在主观上,夫妻分居的原因需要为“感情不和”,因此因夫妻一方工作变动或者出国留学等导致的分开居住并不属于民法典第一千零七十九条所规定的分居。
然而由于社会生活的复杂性及立法变动,分居的认定尚存在模糊地带,法答网上与此有关的疑问有二:一是民法典第一千零七十九条所规定的分居是否包括同室分居;二是民法典第一千零七十九条第五款所规定的“分居”是否也需要满足“因感情不和”的主观要件。
同室分居是否可以认定为法律上的分居,需要考察分居的定义,对此我国立法并无明确规定。在比较法视域下,由于德国对分居同样采取事后认定的立法例,其对分居的定义可资借鉴。《德国民法典》第1567条第1款第1句规定,“夫妻已无家庭共同生活,且夫妻之一方,以拒绝婚姻之共同生活,表明不愿继续维持夫妻关系者,此为夫妻之分居”。依据这一规定,“分居”在客观方面的核心要素在于“无家庭共同生活”,而不在住所上的分隔。同款第2句则进一步表明夫妻即使居住在共同的婚姻住所内,只要双方在住所内分开生活,家庭共同生活仍然废止。上述以夫妻有无家庭共同生活而非以其是否居住在同一住所判断分居客观要件是否满足的做法,更符合分居作为夫妻感情破裂推定事实的角色定位——在现代社会,夫妻感情的维系并不以居住在同一住所为必要,而夫妻之间的经济共享、情感交流以及亲密关系等共同生活要素则是判断其感情状态是否良好的更为本质的指标。此外,在诸如“北上广深”等特大城市,昂贵的居住成本也会对夫或妻一方搬出婚姻住所造成阻碍,如果一律否认同室分居的效力,那么经济能力较低的市民将失去一条重要的摆脱不幸婚姻的渠道,有悖于法律的平等原则。
其次,民法典第一千零七十九条第五款所规定的“分居”同样需要满足“因感情不和”的主观要件。尽管单纯从文意上来看,该条第三款第四项在“分居”前加上了“因感情不和”的定语,似乎“因感情不和”外在于分居概念本身;但是依目的解释,民法典第一千零七十九条第五款的立法目的为通过“判决不准离婚﹢又分居满一年”的事实对夫妻感情破裂进行推定,因而上述事实对夫妻感情的反映至少需要在“质”上等同于民法典第一千零七十九条第三款所列事项。在这一前提下,客观上夫妻共同生活的终止并不足以完全指示夫妻感情破裂,必须在主观情感上加以限制,即需要满足“因感情不和”的主观状态。不过因为此种情形的前提条件为“曾判决不准离婚”,所以在这种情况下(因感情不和)分居只需要满一年即可。
二、分居的时间规定
民法典第一千零七十九条规定的两处分居均需要满足一定长度的时长才可发生法律上的效果,按照通常意义理解,上述时长应该是连续不断地进行所达到的最大时长,且在诉讼发生时,分居状态仍须持续——因为只有现时且长时间的分居状态,方能起到推定夫妻感情确已破裂的作用。据此,断断续续地分居但多段分居总时长相加满足法律规定的期间,或者单次分居持续时间满足法律规定但提起诉讼时已经不在分居状态,均不满足民法典第一千零七十九条所规定的时间要求。
问题在于,夫妻分居期间短暂的共同生活是否会中断上述期间。对此,《德国民法典》第1567条第2款明确规定,夫妻为和好而短暂地共同生活,并不会造成分居期间的中断。这样规定旨在最大限度鼓励分居的配偶双方为恢复家庭共同生活作出努力,避免夫妻双方因担心分居期间重新计算而不愿意尝试和好的局面出现。这一规定具有一定的借鉴意义,在司法实践中,法官可以根据当事人分居后共同生活的原因以及时长进行自由裁量,而非一律将夫妻分居期间的任何接触均界定为分居的中断,以免阻碍夫妻为和好而进行的可能尝试。
三、分居期间配偶双方的权利义务关系
由于分居期间配偶双方家庭共同生活中断,配偶双方的权利义务关系也可能发生相应变化,比如《瑞士民法典》即规定法院裁判分居后,配偶双方实行夫妻分别财产制,《德国民法典》则明确规定家事代理权在分居期间中止等。我国立法上并未对分居期间配偶双方的权利义务关系进行规定,亟待明确。
在人身关系方面,分居期间配偶双方同居义务中断,但仍然负有对对方的忠诚义务以及扶养义务。这意味着分居期间配偶一方重婚或与他人同居,仍然会导致无过错方于离婚时获得损害赔偿请求权;需要扶养的一方在另一方不履行扶养义务时,同样具有要求其给付扶养费的权利。
同居期间的夫妻财产关系主要涉及夫妻财产制度以及夫妻共同债务的认定两个方面。对于前者,分居期间仍应实行夫妻法定共同财产制,但如果配偶双方在分居时签订了分居协议,对夫妻财产制度进行了约定,则应依其约定。对于后者,由于同居期间家庭共同生活中断,夫妻家事代理权亦应随之消解,所以夫妻一方在婚姻关系存续期间以个人名义所负的任何债务,均属于夫妻一方的个人债务,从而与正常婚姻状态下的夫妻共同债务界定有所区别。
此外,配偶双方分居还会产生子女抚养以及抚养费的请求等问题,在法答网上引起一定疑问。对于分居期间子女的抚养问题,最高人民法院发布的指导性案例228号“张某诉李某、刘某监护权纠纷案”曾对此作出解释,该案例认为父母对孩子均享有平等的监护权,但是监护权的行使仍然应符合最有利于被监护人的原则。在该案中,孩子不满两周岁,法院参照适用民法典第一千零八十四条,认为孩子应由母亲抚养为宜,在孩子由一方抚养期间,应当对另一方探望孩子给予协助配合。因此,分居期间子女的抚养问题可以参照适用离婚时子女抚养的相关规定进行裁判。至于子女抚养费的请求,则可直接适用《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典〉婚姻家庭编的解释(一)》第四十三条,如果未成年子女或者不能独立生活的成年子女请求不直接抚养子女一方支付抚养费的,应当支持。
目前,我国虽然规定了分居事实的推定意义,但是在实施层面仍然有所不足,未来可通过发布典型案例或司法解释的方式进行进一步明确。